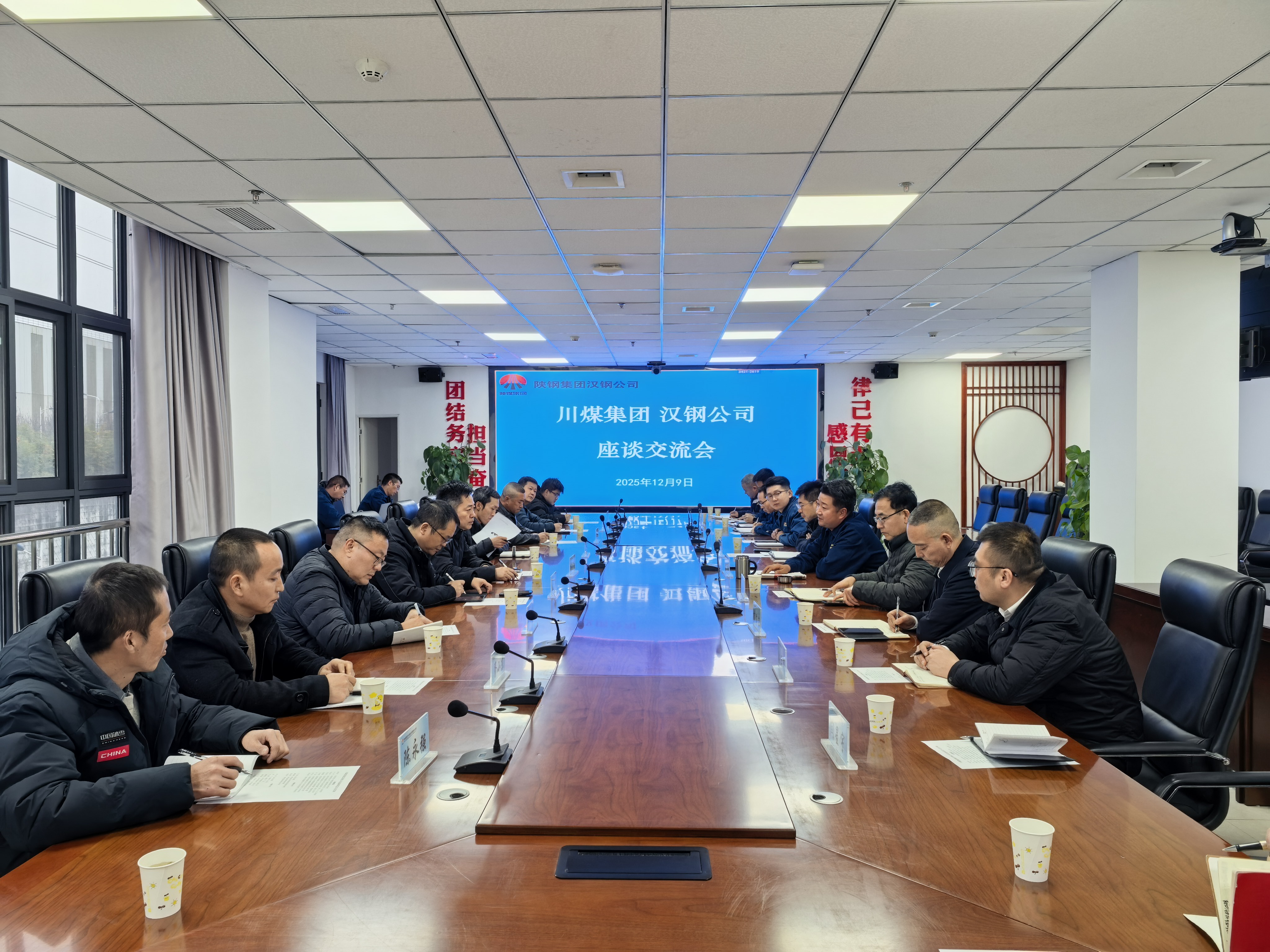炊烟是村庄的呼吸。而母亲的炊烟,是这呼吸里最温柔的那一脉。
我总记得,童年时放学归家的路,是一条被饥饿与期盼拉得细长的小径。书包在背上扑打着,脚步匆匆,眼睛却总不由自主地、早早地望向家的方向。远远的,在那一排排灰瓦的屋顶上寻找,当那一缕青白色、笔直而安详的烟柱,从我家灶房顶上那个小小的瓦隙间准时升起时,一颗悬着的心才“咚”地一声落了地,脚步也随之变得笃定而轻快起来。那缕烟,是我童年世界里最确凿无误的航标,它不言语,却明白无误地告诉你:家在那里,母亲在那里,温热的生活在那里。
走近些,炊烟的模样便清晰起来。它起初是凝聚的、有力的,从烟囱口笔直地向上冒出一截,仿佛积蓄着一股子沉静的劲头。升到半空,被微风一拂,便散了筋骨,袅袅地舒卷开来,化作一片薄薄的、纱也似的青色,依依地缭绕着屋脊与树梢,最后才恋恋不舍地,融化在广漠的、淡蓝的天穹里。那颜色是极好看的,不是墨的黑,也不是云的白,是一种介乎于草木灰与远山岚霭之间的青黛色,干净,通透,带着人间烟火特有的、朴素的诗意。
炊烟的气味,是跟着风向走的。东南风时,那气味便饱满地涌进院子,钻进你的鼻腔——是新米在铁锅里沸腾的清香,是柴草(最好是松枝)燃烧时略带辛辣的芬芳,是腊肉在蒸汽熏腾下溢出的、沉郁的咸香。这些气味分子活泼地碰撞、交融,织成一张无形的、温暖的网,将整座老屋温柔地笼罩。若是北风,气味便显得有些缥缈了,丝丝缕缕,欲言又止,你得深深吸一口气,才能从那凛冽的空气里,捕捉到那一丝熟悉的、微暖的底子。但无论风向如何,只要你闻到它,肠胃便仿佛先于眼睛认得了归途,开始发出安宁的、期待的鸣响。
炊烟升起的时候,是母亲最忙碌也最富神性的时辰。灶膛里的火,映亮了她半边身子,忽明忽暗,像一幅古老的、暖色调的版画。她系着蓝布围裙,身影在蒸汽与火光里显得有些朦胧,却又有一种磐石般的安定感。她熟知每一把柴的脾气,松枝爆烈,茅草温顺,硬木持久;她掌握着水火与时间的奥秘,何时该用猛火攻,何时该以文火煨,全凭指尖的感觉与日复一日的经验。锅碗瓢盆的碰撞声,油脂与菜蔬相遇的“滋啦”声,汤水滚沸的“咕嘟”声,还有风箱那节奏平稳的“呼嗒”声……这些声响,是炊烟无形的旋律,是母亲操持出的、最朴实的交响。那时的我以为,母亲是无所不能的魔术师,能用最寻常的米面菜蔬,点化出一桌安抚五脏六腑的魔法。
而炊烟落下的时刻,是一天中最圆满的句点。当最后一缕青烟散尽,暮色便浓稠地落了下来。饭桌摆好了,一盏昏黄的灯,将一家人的影子聚拢在墙上。饭菜的热气与灯光混在一起,氤氲出一团模糊而温暖的昏黄。父亲卸下一身的疲惫,我们收起所有的顽皮,围坐下来。饭菜或许简单,但经由母亲的手,经由那缕炊烟的召唤,便成了无可替代的、家的滋味。我们咀嚼着,吞咽着,仿佛也将那炊烟里饱含的日光、风霜、期盼与守候,一同咽下,化作骨骼与血液里沉默的力量。
直到有一次,在异乡病倒,独自躺在冰冷的公寓里,高烧带来的昏沉中,我竟清晰地“看”见了老屋屋顶上那缕炊烟。它还是那样青白,那样笔直,那样不慌不忙地升腾着。在幻觉里,我仿佛又变成了那个背着书包、眺望归途的孩子,鼻尖萦绕着松枝燃烧的辛辣与米饭将熟的甜香。一股巨大的、柔软的悲伤与渴望攫住了我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,母亲的炊烟,从来就不只是一缕烟。它是一个坐标,标记着“家”的方位;它是一种语言,诉说着“我在这里”的守候;它更是一条看不见的脐带,无论我走出多远,血脉里涌动的,始终是那缕烟炱化开的、故乡的晨昏与母亲的温度。
那缕青白色的、温柔的烟,早已在我离家的那一刻,就沉潜进了我的生命,成为我灵魂的底色,与我一同在人世间,飘荡,或者栖居。它提醒我,无论走得多远,总有一种味道,可以穿透所有冰冷的时空,引领我,完成一场无声的归根。(生产管控中心 李豪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