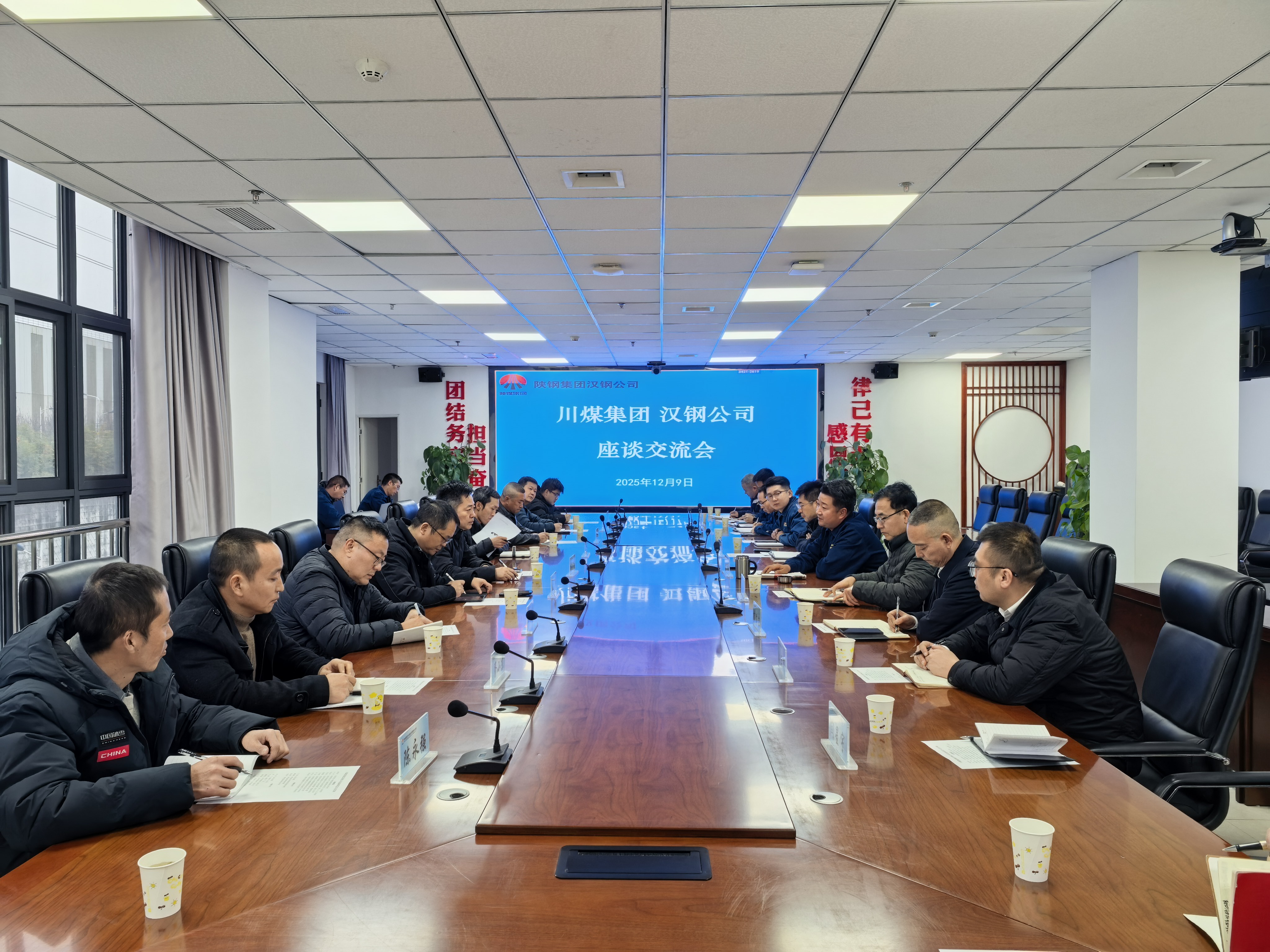三秦大地,在中国版图上是一个最神奇的地方:陕北黄天厚土,革命摇篮;关中四季分明,帝王之都;陕南温暖湿润,人杰地灵。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“关中娃”,第一次接触到“枇杷”这两个字,是因为小时候体弱多病,经常感冒咳嗽。记得有一次吃药打针一个多月,咳嗽仍然时断时续,特别是晚上咳得更厉害。最后看了一位鹤发长髯的老中医,他给我开了一瓶川贝枇杷露,说是具有很好的润肺益气功效,能止咳化痰,润肺补中,对肺热、风热、痰热性的咳嗽、咽喉肿痛、哮喘等有很好的治疗作用,无需再用其他的药物。我坚持喝完了一瓶,咳嗽奇迹般的好了,我还记得那药瓶上的图片,黄黄的枇杷格外醒目,枇杷露那种浓稠甘甜的滋味,这辈子都藏在我的味蕾深处。
再次听到枇杷二字,是在上高中时,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。才知道自己孤陋寡闻,闹了一个天大的笑话,此“琵琶”非彼“枇杷”,不过两种“pipa”真的还有一定的渊源:琵琶中国的一种四弦乐器,音域广阔、演奏技巧繁多,具有丰富的表现力。它在汉末魏初时,名为“枇把”。魏晋时,为区别于“枇杷”二字,改名“琵琶”。当我沉醉于泪水涟涟的江州司马的“忽闻水上琵琶声,主人忘归客不发。寻声暗问弹者谁,琵琶声停欲语迟。移船相近邀相见,添酒回灯重开宴。千呼万唤始出来,犹抱琵琶半遮面。转轴拨弦三两声,未成曲调先有情。弦弦掩抑声声思,似诉平生不得志”的美妙,琵琶的托物言志中时,我更渴望见到那个治好我咳嗽的“枇杷”。由于那时候交通不便,物流不发达,因为枇杷属于亚热带作物,这个枇杷梦,就被秦岭阻隔了四十年。
也许是命中注定,也许是阴差阳错。不惑之年的我为了生计,在二零一三年的四月,第一次跨越了秦岭,在满目的油菜花中,落脚到了定军山下,继续自己钢铁之梦。勉县,属于汉中盆地的西部,亚热带气候,风土人情,生活习惯跟川人无异。作为吃了四十年吃面的“关中娃”,一下子对米饭腊肉、热面皮菜豆腐难以适应。当每天拖着疲惫的身躯倒在潮湿的床上,心里五味杂呈,既有轧线顺利投产的喜悦,又有说不完的思乡之苦。不过当我看到一种不认识的树,五月的枝头,黄澄澄的果实一咕噜一疙瘩,实在诱人,我环顾四下无人,偷偷摘下一颗入喉,是它,就是它,那种埋藏在我记忆深处的记忆豁然开朗,那是方岳“击碎珊瑚小作珠,铸成金弹蜜相扶”;那是“绿萼经春开笼日,黄金满树入筐时”;那是戴敏“东园载酒西园醉,摘尽枇杷一树金”所写的枇杷。我终于看到真正的它了,这一树的金黄,这一树的酸酸甜甜,我吃了一颗又一颗,大快朵颐,竟然忘记了此时此刻我是个小偷。当一位老人拍着我的肩膀时,我才反应过来,连忙掏出几元钱递给老人,老人微微一笑,用本地话说了几句,我虽然没有完全听懂,但从老人和蔼慈祥的笑容里,大体意思我懂了,枇杷到处都是,喜欢吃就行,还给我摘了几串又黄又大的。此刻远处的定军山迷蒙在袅袅氤氲里,而我,一颗郁闷的心,却渐渐地亮堂起来!
冬去春来,枇杷花开果熟八载,满树金黄的枇杷,那酸酸甜甜的独有味道慢慢改变着我的味蕾,我习惯了热面皮的辣,鱼腥草的腥,浆水面的酸。我更熟知于轧线上每一台设备的振动和温度,跟它们就像陪伴多年的朋友,彼此默默地守望着,我给它们拂去身上的积尘;给它们更换坚固的备件,给它们输入纯净的油料,使它们能够更加灵活运转,轻松轧出一卷卷盘圆、一捆捆螺纹。走进高铁,走进桥梁,走进千家万户。我也在与定军山酸甜的枇杷和金刚铁骨的设备相互陪伴中,度过更加沉稳丰裕的天命之年,用自己荣辱不惊、坐怀不乱的内心,去看秦岭的蕙兰盛开,去看汉江的一江东流,不断完善自己,充实自己,就像枇杷一样,前年秋天开花,蛰伏一冬,来年秋天用那一树金黄酸甜的枇杷,给人们带去美好和康乐。(轧钢厂 王辉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