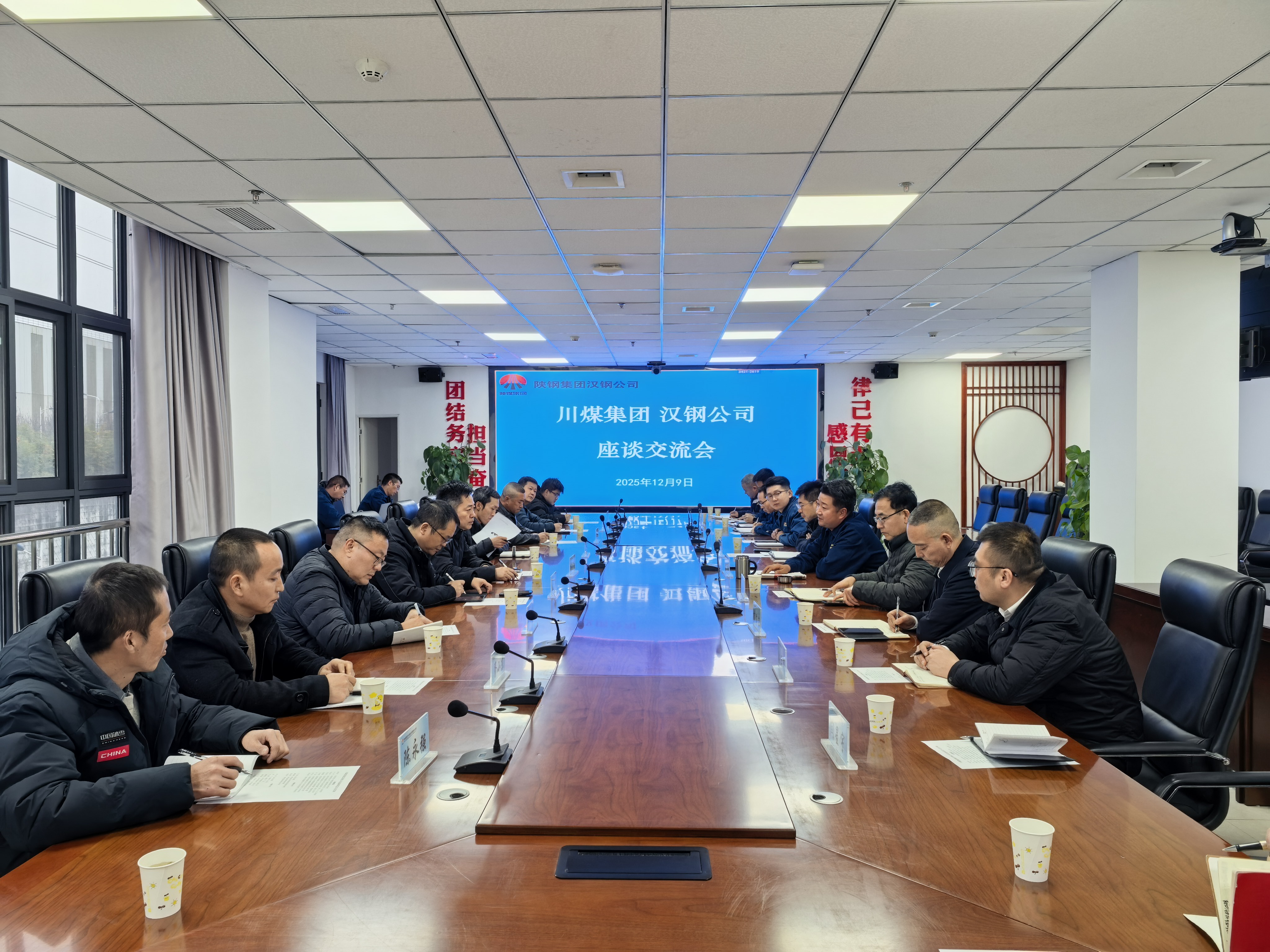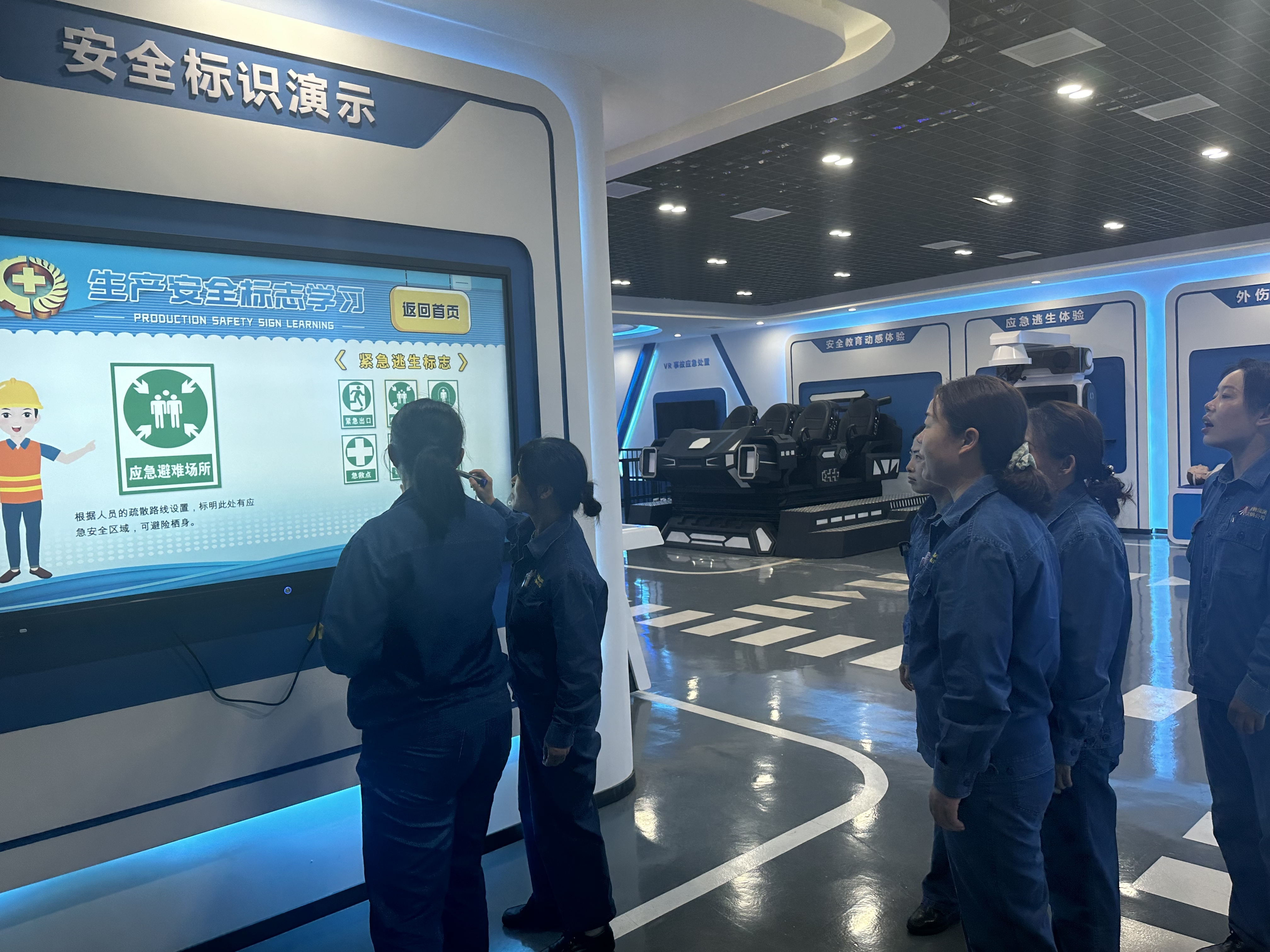刚进腊月,父亲就频繁的来电话,电话里念长道短,在谁家买了吊边土猪肉,谁家送的老母鸡养在家里还没杀,忽而又说起家里把红纸都买好了,就等我回去写春联。
说到写春联,从高中时候起,老家院子里各家各户的春联都由我来写,已渐渐成为和过春节走亲戚一样,是约定俗成的事情。春节过后,邻里亲戚们来家里做客,对着我写的春联品头论足一番,也是父亲暗地里偷偷骄傲的资本,但想到厂里春节期间放假安排,我还是不由得犹豫了一下:“大年当天才放假,今年怕只能赶回家吃团年饭了。”
父亲听了后,只“哦”了一声,半晌才说:“我知道了。”
我知道父亲心里有点失落,正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安慰他的时候,他反倒主动把话题岔到一边去了。这么多年了,父亲总是这样,一心为我考虑,把什么都担在自己身上,即使是过年不能提早几天回家,他也表现得好像是因为他的原因造成似的……
不知怎地,主题又一转,父亲在电话里突然说道:“你晓得不?袁老汉前几天过世了。”
“过世了……怎么死的?”
出来工作以后,每年回家,家乡都有人死去,仿佛已经成为惯例,见得多了,我已是云淡风轻见怪不怪了,但听到袁老汉去世的消息,等我从云淡风轻中迅速反应过来,还是一阵说不出的惊讶。捧着电话,有一种肃穆的感觉围绕着我,就像我是在一出葬礼的现场。
“可怜老汉能了一辈子,临死的时候,连个送终的都没有,一个人悄悄儿死在老庄子房屋里头。”
“他好几个儿女,咋会没有人送终?”我问道。
“哪个晓得得的啥怪病,头天晚上还好好儿的,在儿子屋里喝酒,喝完酒黑天半夜非要回老屋,第二天天都快黑了还没看见人影儿,屋里人撵到老屋去找,发现门拴着,打不开,喊也喊不答应,把门撞开,才看见袁老汉躺在床铺前头,光身子缩成一个疙瘩,冻得梆硬,我们去帮忙入殓的时候,胳膊、腿都掰断了,才勉强装进棺材。”
“去年回去还好好儿的,怎么说死就死了?”我不相信一般地问道。
“上了年纪,人都一样,哪晓得哪天说没就没了。”
我突然陷入了沉默。又是整整一年没回家了。上次过年回去还见过袁老汉,怎么突然就死了呢?
世界上再也没有袁老汉这个人了,当我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,仿佛我突然意识到这世界有一个巨大的漏洞,好多事情就从那个漏洞里永远地消失了。以前我从没过这种感受,忽然意识到如果有漏洞的世界是真实的,那之前我理解和接触的那个世界,仿佛就不真实了。
我和袁老汉的小儿子是很要好的同学。从小学开始,我们就在一起读书,熟悉得就像可以穿一条裤子。之所以说是袁老汉的小儿子,是因为他还有三个姐姐,在上个世纪计划生育政策异常严苛的年代,一个男娃有三个姐姐,那么他们的父母所要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象的。听别人说,当年袁老汉第三个女儿出世的时候,连县上的领导都出动了,结果到了袁老汉家里,却连一条板凳都没得坐,全坐在道场边的石头上。因为家里早就被乡上的干部搬空了。
就在那种家贫如洗、计划生育政策又严苛如山的情况下,重男轻女的袁老汉到底得偿所愿养了个儿子——就是那和我可以穿一条裤子的同学。并且,袁老汉靠种着几十亩山地,愣是把四个孩子都送进了大学学堂,如今,三个女儿都是人民教师(不用想,女儿们也是遵行袁老汉的要求而选择了教师这个神圣的行业,而袁老汉肯定是受那个年代铁饭碗思维的影响。人民教师是毋庸置疑且农民出身的家庭能够够得着的“铁饭碗”);至于小儿子,则毕业于建筑专业,如今在建筑公司任经理一职。村里人说起袁老汉,说起袁老汉如何供应四子女上了大学,心里都是大写的、五体投地的“服”——然而,这并不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。
我钦佩他的,是小学没毕业,一个地道的庄稼汉,却写的一手好字。那时候农村流行写“香火”,也就是各家正屋里的中堂,在香案后面的墙上挂着大大的“天地国亲师位”,方便时时拜祭。而当时乡里的“香火”十之八九都出于他手。出于对书法共同的热爱,如今回想起来,他写的“天地国亲师位”,那一横一竖一勾都宛在眼前,仿佛刻在我的脑子里,永远也无法抹去。
除书法之外,他还精通乐器,吹拉弹唱,样样在行。尤其唢呐吹得一绝,乡里但凡红白喜事,请班房时都少不了他。乐队奏响的时候,他鼓起腮帮子,能连续吹两个小时不换气儿,我们小时候,就喜欢围在他身边,不听唢呐响,就看他一鼓一鼓的腮帮子,从来看不厌烦。
他还是一个十里八乡的好木匠。小时候,村里人经济宽裕一点后,人们都喜欢给家里置办几样像样的家具,用桐油油得锃亮,看得人心里踏实,就像家里储了黄金。农忙之余,袁老汉就马不停蹄地给乡里乡亲做椅子,做风扇,做腰盆……几乎没有空闲的时候,而且找袁老汉做家具,还要预约,因为他做的腰盆,结实耐用,要十来个人一起,才能把铁箍箍上去,他做的风扇,简直可以当传家宝一代一代传下去……那时的家具全是实木打造,卯榫契合,他给我们家做的柏木椅子,用了十几年,仍然坚固如初,就像昨天才做出来一样。
袁老汉是我们村里真正称得上多才多艺的人,他的手艺仿佛是娘胎里带出来的。后来随着年纪渐长体力衰退,丢下许多手艺之后,他在镇上开办了门面,专门给亡人刻石碑、扎花圈、扎灵房、扎汽车、扎金童玉女,几乎垄断了当地这个行业,没有人不说他心灵手巧的,供货紧张的时候,还会出现几家人抢同一批花圈灵房的局面……
就是这样一个勤劳、朴实、多才多艺的人,用双手和才智营造了一生的人,也终于不在了。我倏忽间杂乱地想到许多事,想到他的小儿子——我的同学,已经失去他的父亲;也想到他的结实、丰厚、又短促的一生;还想到他们那一辈人,他们走过的那些年代;甚至还想到新世纪我们上场的时候,也和他们一起生活在同一时代,但是,我们一直走在康庄大道上,而他们,仿佛一直走在路旁的深沟里……
仿佛要用好些年的时间才能想到那么多事,但就在那么短短的几分钟里,我的大脑像奔跑的高铁般,匆匆地领略了那么些事物。事实上,也真有一种长时间坐高铁的感受,既轻盈,又沉重,还伴有疲累。我不知为何会疲累,父亲在电话里不断地说着什么,我竟也能沉静地应答,等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应答的内容时,我发现自己正奇怪地站在马路边的一棵柳树下面,以至于我不得不多看它两眼,正因为如此,仿佛它非常重要,以至于我永远都不会再忘记它似的。
“咋不说话?没事就挂了。工作要紧,对子(春联)写不了了,我就去买几幅印刷的算了。要是袁老汉没死,还可以请他写。”顿了一会儿,父亲冷不丁又说一句:“我不喜欢印刷的对子。”
“要不,我把对子写好,寄回去?”我说。
“寄回来?”父亲想了不到一秒钟,“算了,寄回来运费都要二十多块,买对子的钱都够了。”
二十多块,也就是出去喝酒打一次出租车的钱。但我无法跟父亲解释和争辩什么,如果能从开支里节约一分钱,他就会想办法给我节约一块钱出来,这就是我的父亲。
“那就买吧,还是晚些买。如果能争取早几天回来,我就回来写。”
“行。”父亲愉快地答应着,“那就不说了,你忙吧。”
父亲挂断了电话,我继续在马路上走着,满脑子里还是袁老汉的影像。不对,还有父亲的影像:他的脸,皱纹,黑黝黝的皮肤,屋檐下他不算矮小但已不像年轻时那般结实的身体,还有那灰土土的衣服。一切是如此清晰,我忽然明白过来,我为什么会觉得疲累,那是袁老汉一生的疲累,也是父亲一生的疲累。父亲和袁老汉,本是一代人啊,他们经历和付出的,不正是为我们这一辈人而苍老吗?
我还可以继续沉浸在疲累中,一直沉浸下去,但肯定不会超过明天,甚至不能超过今天夜晚,因为我也有一生的路要走,父母亲已经老了,但还把力所能尽的一切,就算是一根火柴,也要留给我,那么,我必须活出年轻人应有的样子来。
冬日的阳光,带着清冽的寒冷,我还在马路上走着,突然就想回家了。(生产部 田肇运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