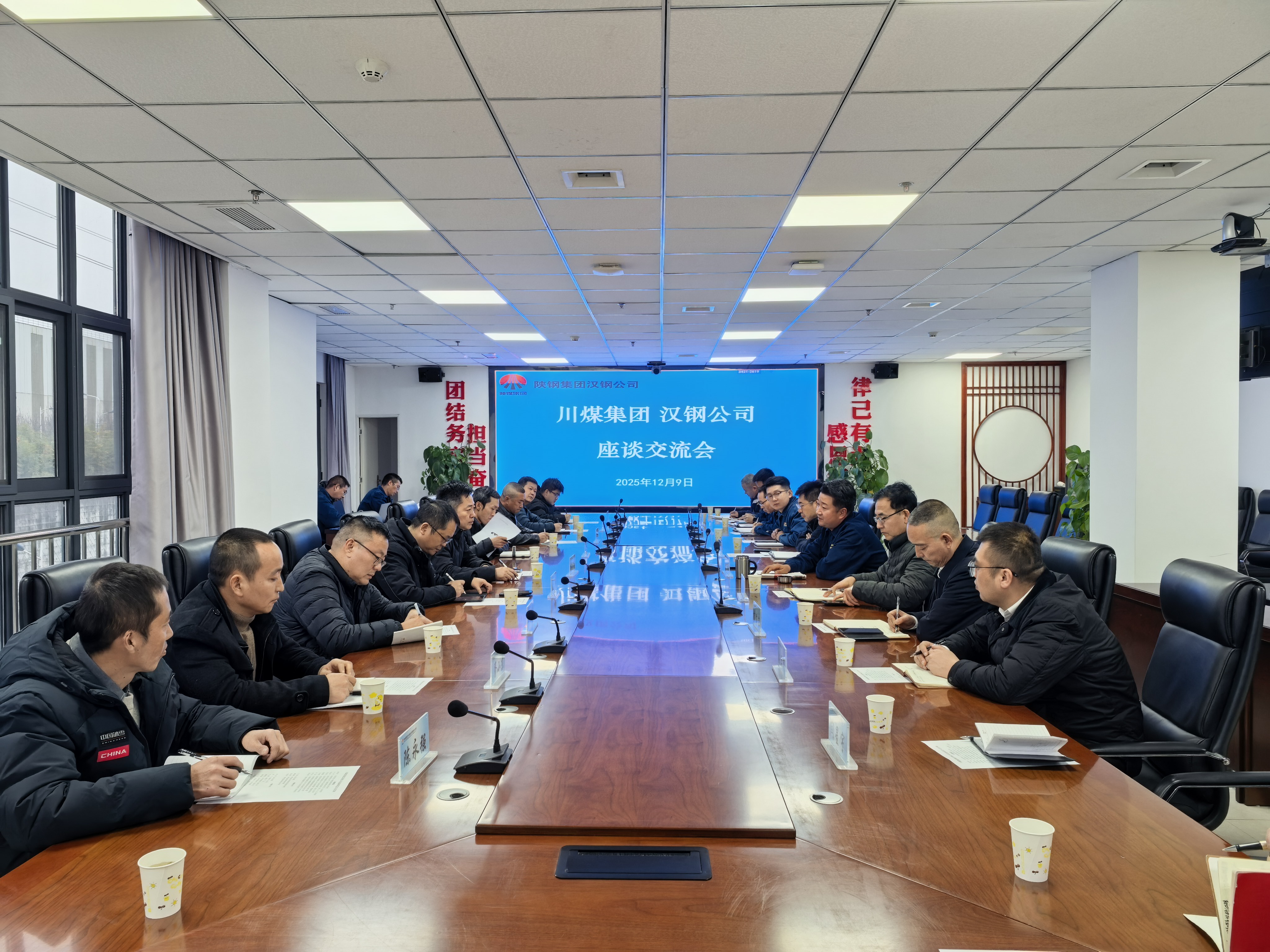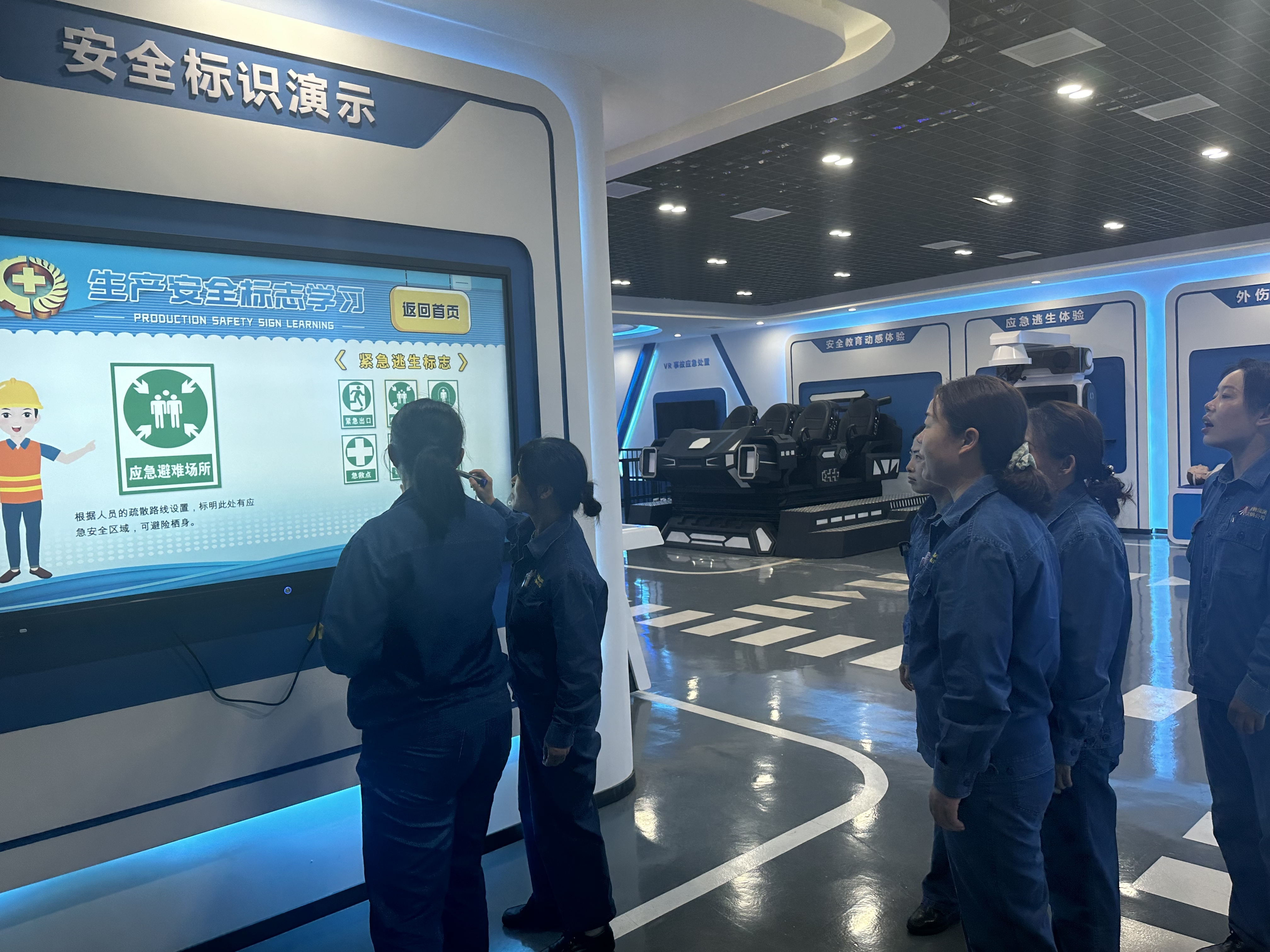水杉,裸子植物,杉科,高大落叶乔木,小枝对生,下垂,叶羽状复叶,线形,交互对生,长1-1.7厘米,雌雄同株,生有球果,种子扁平,一种源自中生代白垩纪的古老稀有树种,不仅树姿优美,而且材质优秀,是著名的园林树种和产材树种。
我的家乡,古城西安南部,樊川古道上,一个古老的村落——寺坡村,村口就有这么一些高大俊秀的水杉树。这些树是上世纪70年代,村子里的县人大代表兼村长——赵世贤为了美化乡村,领着村民一起栽下的,距今已有四十多年的历史。
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,不管是刮风下雨,寒来暑往,这些树都像是两列身着军装的迎宾礼兵般,笔挺的矗立在通往村子里的大道两旁,迎接着八方来客,像母亲一样,呵护着村里的男女老少,常年为他们送去精神的慰藉。
春天,这些树的叶子还不是很稠密,青翠欲滴的样子,层层叠叠,呈三角形,从底部延伸到顶端,远远望去,像是一个个耀眼夺目的翡翠宝塔,无论是远方的客人,还是村里的乡亲,走到这里,顿时就会有一种碧翠怡人,神清气爽的感觉;夏天到了,树叶的颜色便会由原先的翠绿变成深绿,大小形状也不像原先那样棱角分明,而是在半空中连成一片,遮天蔽日的将整个路面覆盖起来,在田里劳作了一天的乡亲们,或是在打麦场上碾场的人们,走到这里都喜欢坐在树下,嗅着水杉树清香的味道,纳凉、聊天、休息个把钟头再回家,那种侵骨的舒爽别提有多美;秋天里,水杉树又会变得像一位端庄秀丽、成熟稳重的绝代佳人,着一袭华贵的橘黄色锦袍,迎风起舞,顾盼生辉,一袭秋风来到,它们又似天女散花般,洒下一地黄花,惹得如我这般的爱美之人频频回顾,怜爱疼惜;到了冬天,美丽了大半年的水杉树叶子全落了,但它们却以另外一种清瞿顽强的风骨呈现在人们的眼前,它们的枝丫不像别的树木,枝枝蔓蔓做写意状,主杆和枝丫一律以一种笔直整齐的形态伸向蓝天。大概是受了这些树的影响,村里的村民也像它们一般养成了果敢刚毅、豪气直爽的性格。
这些树在我很小的时候,还只是一些小树苗,根部只有碗口那么粗,最高也不过六七米的样子。那时村里有不少饲养山羊的人,而羊对吃的东西又是比较讲究的,湿的、脏的不吃,有怪味的也不吃,因此村里的孩子们放学后有一项重要的工作,就是爬树给羊折树叶吃。北方常见的有一股青草味的杨树叶子是首选,数量稀少、清香怡人的水杉树叶,那是不可多得的美味,于是村口这些美丽的水杉树下便时常会响起孩子们的欢声笑语,他们比赛看谁爬得最高、最快,看谁折的树叶最多、最好。
如今,这些树已长成了参天大树,最高的有二三十米,根部比一个成年人的腰还要粗,但数量却从最初的130株减少到了现在的63株,一半多随着时间的推移,不知什么原因已经没有了。前不久回乡探母时,再次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,见到村口那些伴随了几代人成长的水杉树时,我的心紧紧地揪在了一起。
大概是为了美化乡村环境,滋养了水杉树40多年的路边排水渠和树的根部,全部被冰冷的混凝土封了起来。在缺水的黄土高原地区,没了排水渠贮藏的雨水,喜欢湿润环境的水杉,能活多久?明年还能不能再看到它们美丽的身影?我的心里不免担忧起来。
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速,家乡发生了很大变化。原先泥墙蓝瓦、苔痕阶绿的乡村景象,变成了现在和城市一样,到处都是钢筋混凝土的乡村,这样的家乡没有了儿时古朴、原生态的样子,使得如我这般的游子,再回到家乡时,竟找不到家乡记忆中的样子,也找不回儿时的快乐和往事,缺少了这份情感的纽带,内心的落寞油然而生。如今再回到家乡,记忆中除了大队部那座三层红砖小楼外,就只剩村口这些见证了家乡几十年时代变迁、环境变化,迎来送往了一批又一批乡亲走出去再回来的水杉树了。
画家陈丹青曾在一次访谈节目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,他说:“现在为什么很少看到,有哪个离开家乡、事业有成的人,为家乡做点事?”的确是这样的,很少有这样的事见诸报端。我想,这大抵是因为家乡因为时代的进步,不再是他们记忆中的样子,那份对家乡的感情也因此而缺席了。我无意于对家乡的发展说长道短,只是希望家乡在发展的同时,别忘了家乡的游子,为他们多留一些家乡的印记,待他们回乡寻根问祖时,能找寻到一些曾经的记忆,让他们的灵魂多一些安慰和温暖。(动力能源中心 赵娟妮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