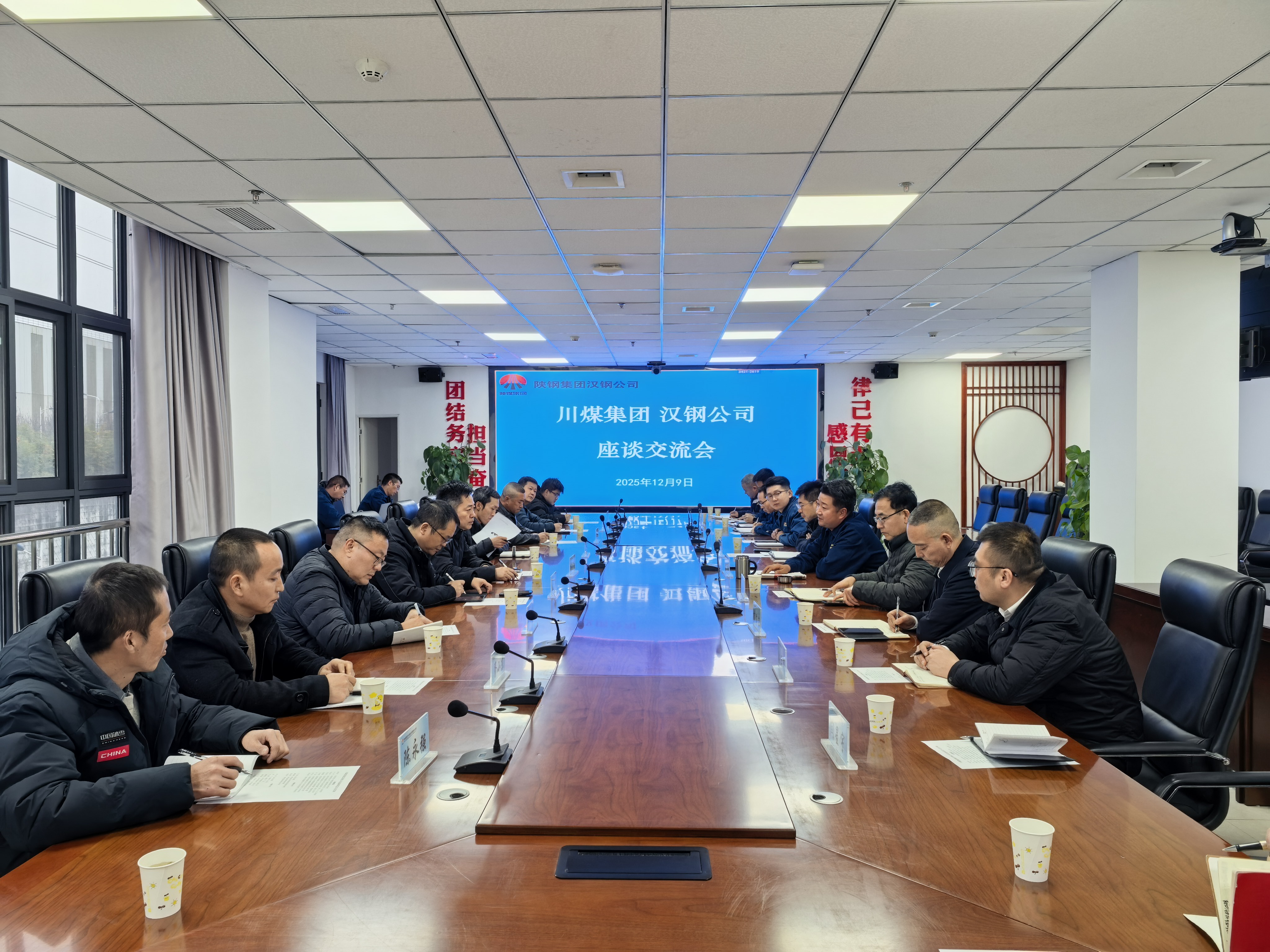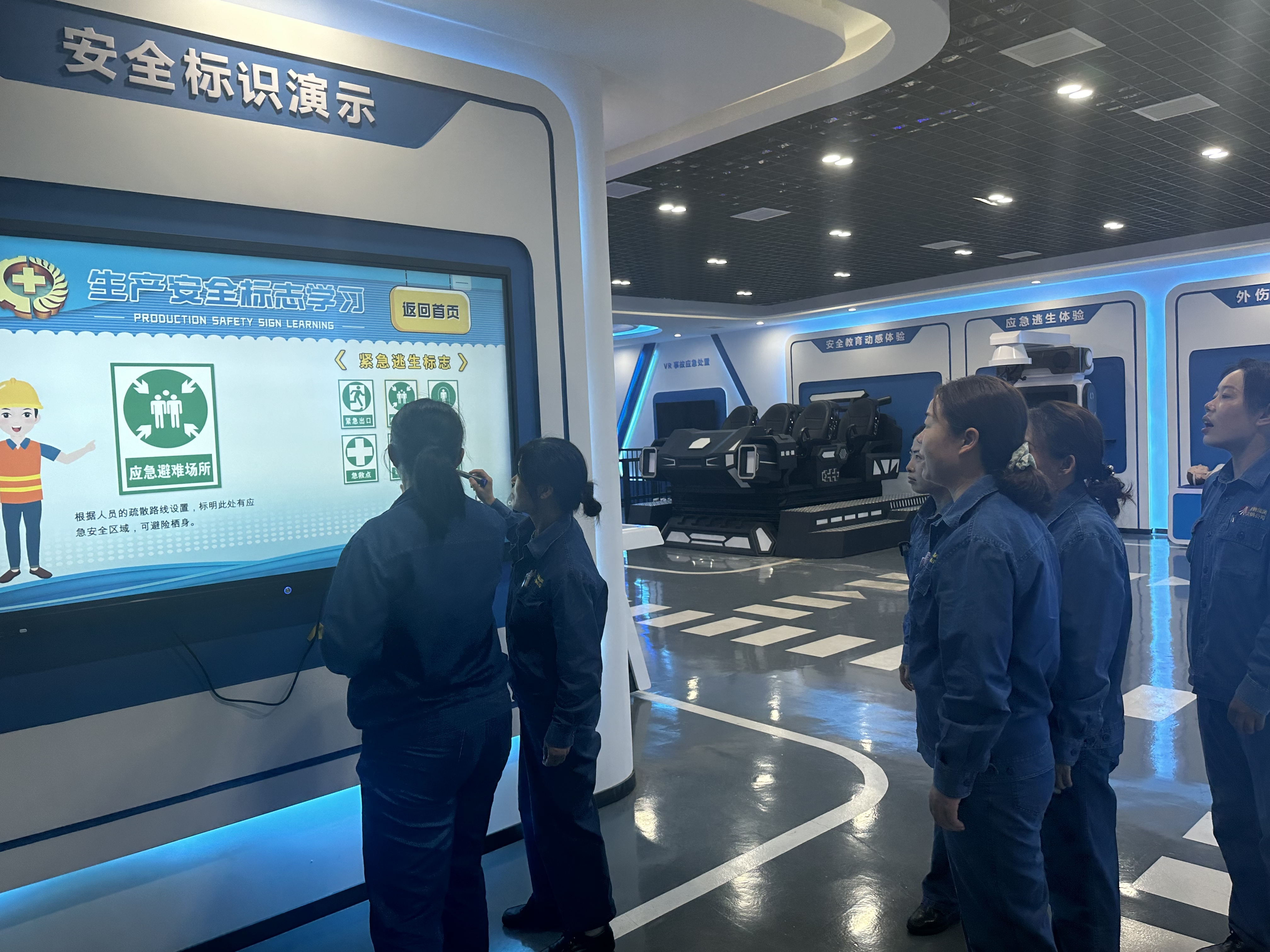入冬,我便期待着一场鹅毛大雪的到来。奈何左等右等,这雪,扭捏着总是不来。家里长辈说今冬是暖冬,日头高挂,哪里寻得见半丝大雪将至的迹象?他们不晓得,我有多盼望。可我真正期待的单是那雪吗?并不。是那飞雪来时带给我无限珍贵的儿时回忆。它更像是一种信号,使我暂别杂冗,放空身心。
如今等到这迟来的大雪,置身其中,只一瞬,我便能感受到,从前因雪带来的欢乐,在我全身血液中翻滚沸腾。脑中斑驳的画面变得清晰,我甚至能忆起尘封往事中关乎大雪的许许多多熟悉的味道、触觉、声响等等。
冬雪来了,小孩子最是欢喜的。他们不惧严寒,成群结伴奔向白茫茫的世界,滚雪球,打雪仗,堆雪人,顽皮的会将同伴引到树下,猛地摇动树干然后迅速跑开,看着树下落满雪花的小人儿哈哈大笑。攒捏雪球的小手被冻得通红,可他们才不要管这些,只顾着将手里的冰球摩擦得如同光滑的水晶球一般才算好,相互比较着,玩闹着……
天热渐暗,大人们则是紧裹棉衣,纷纷出门找寻贪玩的孩子回家,一面斥责,一面紧握着泛红的小手揣进自己的兜儿里,深一脚浅一脚地踏雪归家。
这便尽兴了么?远远不够。
回家后,端着饭碗也要放在彼时于孩童而言略高的窗台上,吃着,看着窗外的雪渐厚。大人们不能理解,雪,寻常的雪,哪里来的这般的吸引力。此时孩子小小的脑袋里,想象着关于雪的一切天马行空奇幻绚烂的故事,美好,正在他的心中生根发芽。坐在书桌前打开日记本,小孩子忽地想到“银装素裹”,一笔一划写着,以生稚的姿态记录着,冬日的童年。
屋子里昏黄的电灯亮了,炭火盆里泛出蜜糖样的香甜。贪吃的孩子往往有敏锐的嗅觉,搁下笔,跑去火盆边等着,盼着,小心翼翼地从大人手里接过垫着厚厚棉纱布的蜜薯,吭哧吭哧跑掉了。
又是窗台边。
手里是烫得直冒热气的烤红薯,孩童心急着,呼呼直吹,玻璃窗被蒙上一层细细的白雾。腾出手来抹一把雾着的玻璃,背对着光源,他看到窗外的雪,竟是金色的,旋动着,飘落着。
夜深了,小孩子睡熟了,手边是用铅笔勾画出的怪异滑稽的雪人。
我被跌落在鼻尖的雪“烫”醒,耳畔隐约传来母亲的斥责:“快回屋,冰天雪地的,不像样子!”我扭头应着,两脚一深一浅踏着雪,走向母亲,将她粗砺的手揣进我厚厚的羽绒服,缓缓归家。
一切都回来了。(炼钢厂 周鹤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