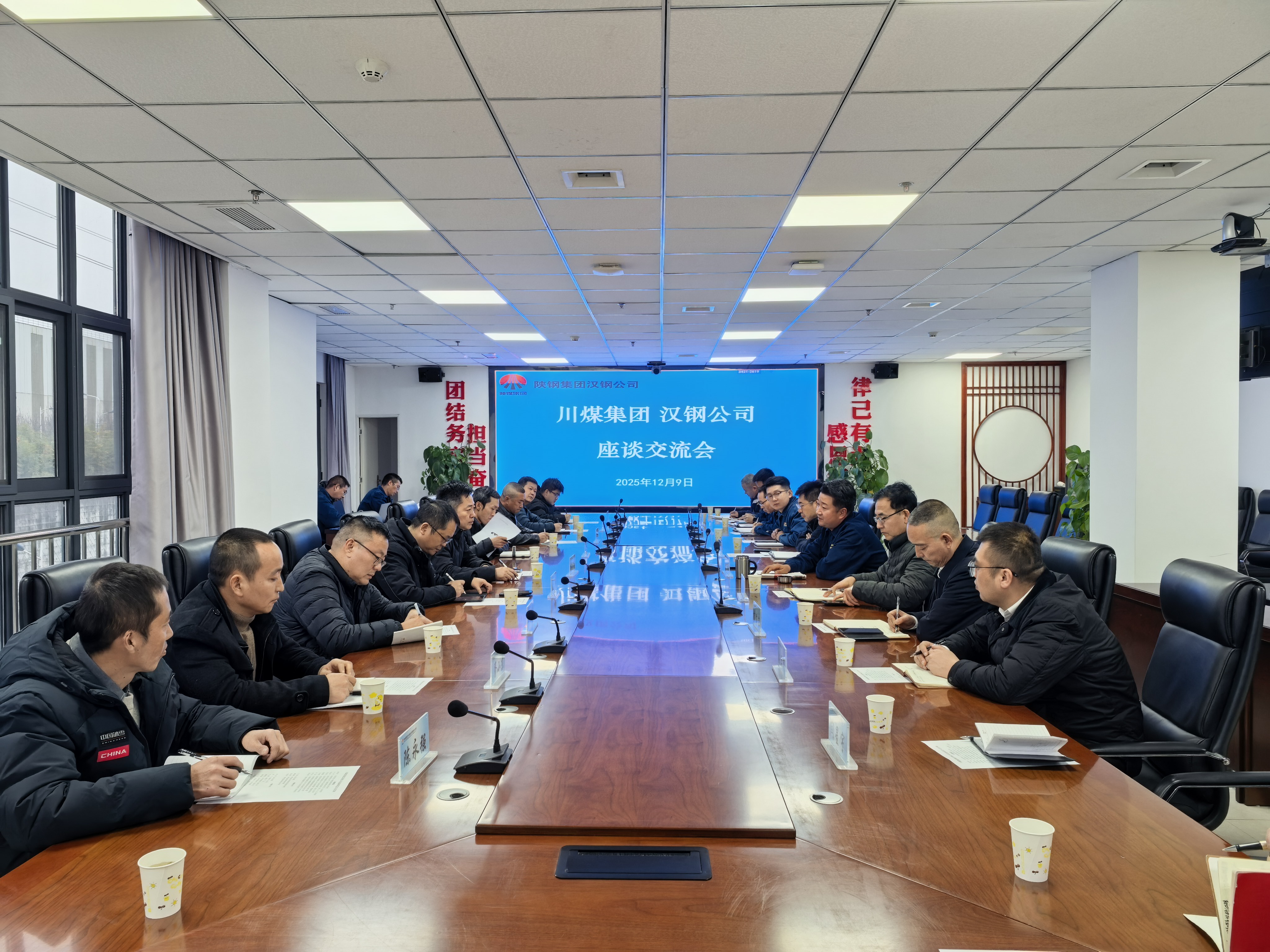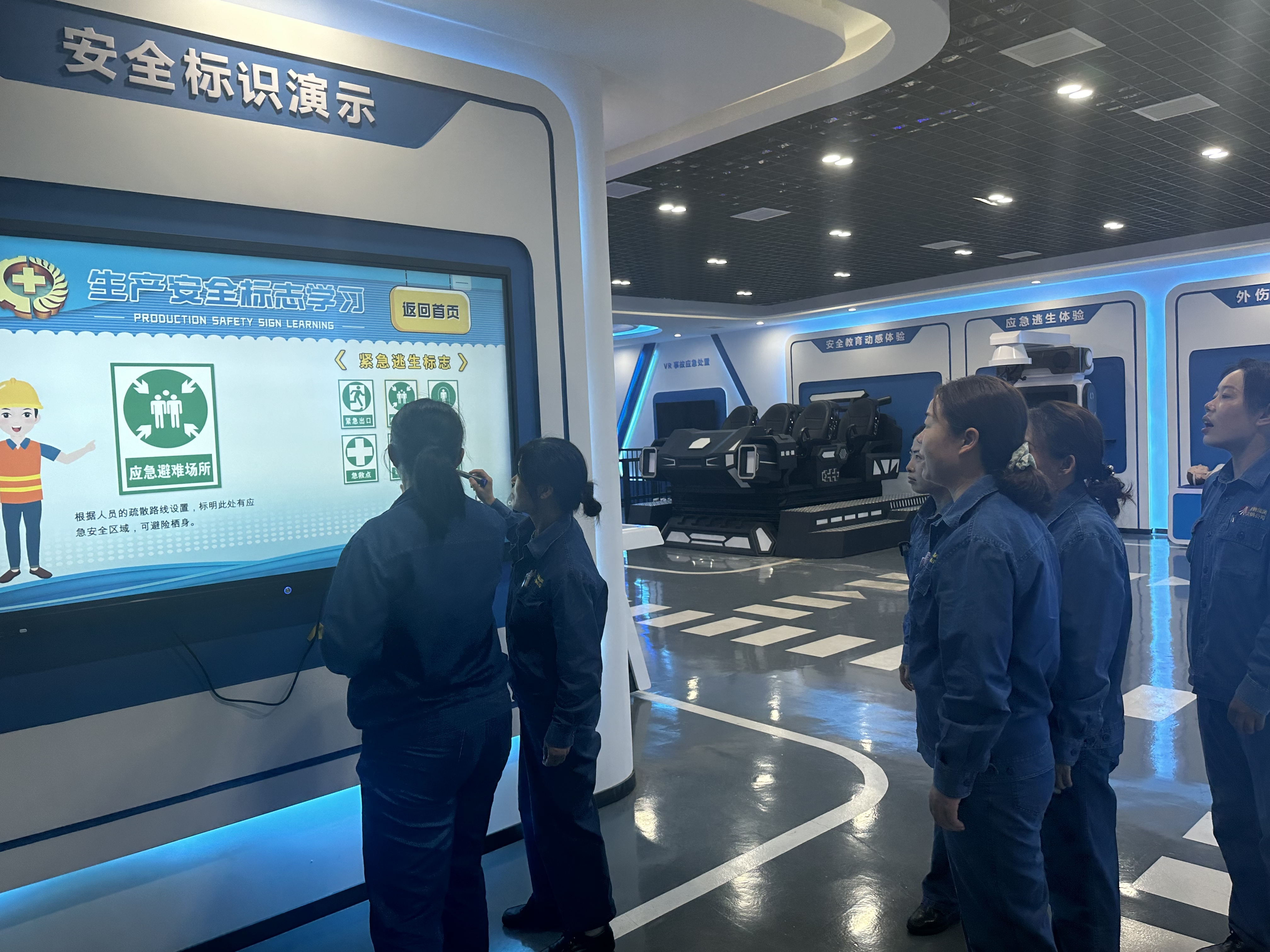我和我爸一向有时差。
小时候记事起,我见他的时候总是很少。偶尔他骑两个小时的自行车从县城回到家,我却已经睡了,天不亮,又赶着自行车去上班了。无垠的山路,隔着三十多里的时差。
家里田地树林交公了,他的单位也改制了,我也要上小学了,一间三十平米的筒子楼拿一道窗帘分开的两居室,最终让一家人蜗居在这陌生的县城。白天他去外面的工地当学徒,晚上在已经倒闭的厂子绑钢筋,三个小时十一块钱,手快计件。我见到的总是他无尽的疲倦和动辄就是巴掌的打骂。小心翼翼的害怕,隔着只有一道帘子的时差。
生活慢慢好起来了,我爸带班了,也能接一些小的私活了,我也上高中住校了。他的时间不再像几年前那样赶了,但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,训斥和责骂是常有的事。青春期的叛逆尝到了和他对抗过后的快感,冷暴力也是让我内心暗爽的最简单途径,遇到我想听的还则罢了,不爱听的我就回出租房了。他也不能像小时候一样抽我了,我已经比他高一个头。无言,是摆在我们面前现实的时差。
我喜欢了一个女孩,是我们班同学,坐在我的左手边。我们没有像其他情侣一样高调示爱,每天都埋头数学和理综的试卷,我们都在认真备战高考,甚至比以前更努力,即使只有一个过道的距离,我们都相互不理。
高考完了,我爸还是知道了,我能感觉到他有什么要和我说。
“你,上学分心了?”
“没有。”
“那这是啥?”那是一张她写给我的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:我们一起报西安吧。
“你翻我东西了?”
“我翻你东西?那你就别去上学了,我给你把媳妇取了就对了,还上什么学?啊?”
“我借你10万块钱,工作了就还你。”
终究那一巴掌没有打下来,我对着他,他看着我。沉默,隔着我们父子间深深的时差。
大学我最终还是去了,我们之间基本没有话可说。
再次说到我的话题,依旧只是之言片语。
“你们,还在联系?”
“嗯?哦,嗯。”
“后面会结婚?”
“是。”
“我没上过学,但是我知道学生这种一般都没有太好的结果,最后走不到一起的基本没有,这一辈子的事,你,考虑清楚。”
“我早就考虑清楚了。”
“那明天让你妈炒几个菜,让她来家里玩吧,你妈准备了个红包,时间长了,别把我们家看小了。”
我爸没上过学,却写的一手好字,劲道方遒,他做人也是一样。
那一年,我大三。我诧异万分的不只是他突然的一番话,还有就是后来的一些安排。这,我也说不上来。
直到前年的一天,妻子给我打电话:“爸从架子上摔了,很严重,在中心医院。”
我发疯似的赶到医院,从未觉得如此的惶恐。我周围的人全都变得模糊,远远近近的人潮声拉扯到很长、很长,生腥味压着我的鼻腔让我忍不住想要呕吐,流到嘴边的全是咸甜的口水,心肺抽的厉害,气管堵得发慌,我忍不住战栗。我从未如此厌恶医院里那生冷的气息,也从未如此迫切的渴望着医生的检查。
我叫不醒他。
我爸在他21岁时送走了我爷爷,27岁时埋了我奶奶。
坐在医院的台阶蜷缩成一团,川流不息的大街和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,无力的我连一只香烟都抽不出来,我把它们揉成一团丢掉了。很多年没有流过眼泪,那一天我流了很多年的眼泪。
我守了三天三夜,我害怕,害怕这一别便是永远,我从未如此需要他。
生与死的时差却是那么真真的真实,好在一切都往顺心的方向走了。
这两年我爸终于是闲了下来,辛苦了一辈子的人,身子变得单薄。在家带带孙子。我因为工作的原因,和家里聚少离多,我们的时差倒了过来,我也变成了年轻时的他。
我爸头发也越来越少,花白的青丝也越来越多,也总是打电话让我回去,很少喝酒的他每每也挨着我坐,让我陪他喝上几杯。
按时吃饭,多喝水,我们一切都好到的,只是有好久都没见你了。
我已经泪流满面了。(炼钢厂 邓锐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