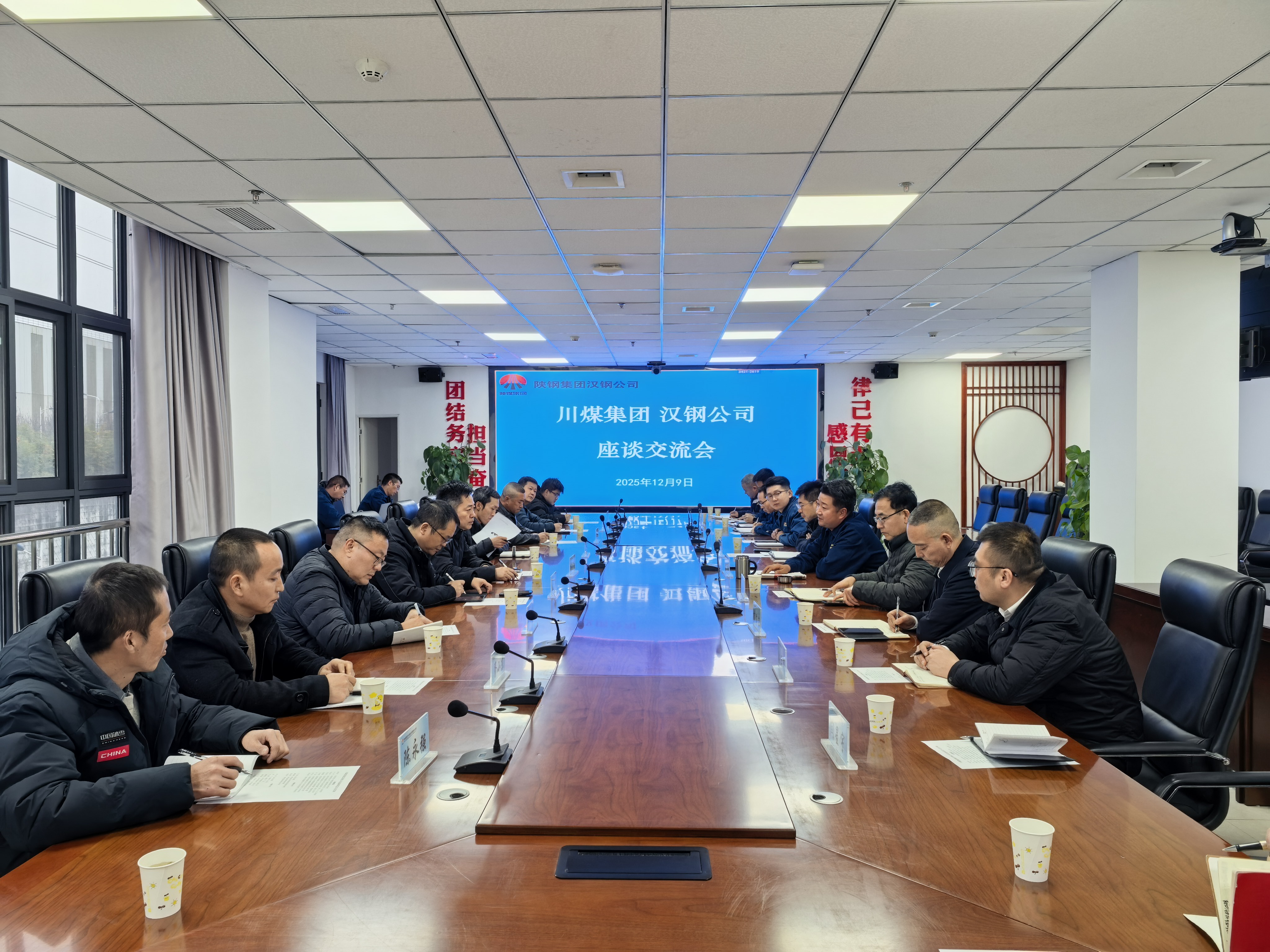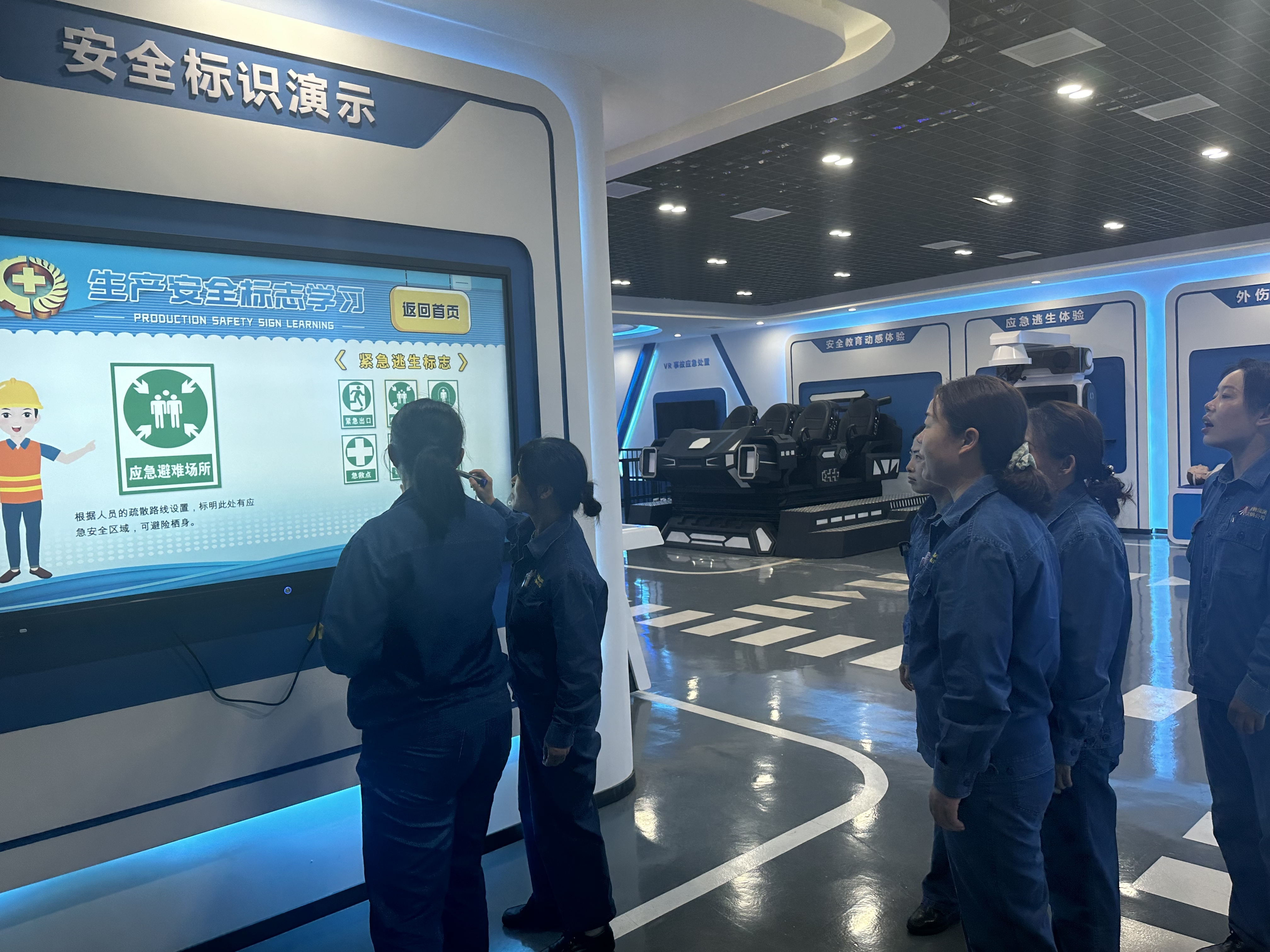前几天刚过了大雪节气,上班从生活区到生产区,一路上绿树红花,我不由想起了老家的枝枝丫丫,这季节,定然是凛冽的风吹尽了树上的最后一片黄叶子,如果有雪,那便是另一幅千里冰封万里雪飘的北国风光了。身边三三两两经过的孩子,无不穿着时髦的衣裳,我看着他们的脚上,都是炫酷有型的运动鞋或是漂亮精致的小皮鞋,手上是五颜六色各种样式的手套。穿过时光的隧道,我似乎看见我的童年时间和童年的小伙伴,冻得红扑扑的脸蛋,皲裂的手背,脚后跟的冻疮……
我没有冻过手脚,这大概与母亲有着莫大的关系。每年不到10月份,母亲就给我预备过冬的套袖与棉鞋。北方农村人管冬天给手取暖的物件叫套袖。其实再普通不过,就像棉衣接了一段袖管一样。只不过是单独做的而已,脱戴方便。母亲总是用带花色的棉布给我做套袖,一般是碎红花布,夹层絮上洁白的棉花,里面那层一般是旧棉布,这样柔软。别的孩子的套袖是齐的,母亲做的总是有一部分带点弧度往前延伸了一大截,新套袖上手的时候,仿佛由外暖到内,直到五脏六腑。因为带着弧度前伸了一截,写字时手背也是暖和的,仿佛母亲的手在温暖地抚摸着我。
棉鞋是冬天的必备之物,否则漫长而寒冷的冬天可熬不住。为了省电,家里的电灯只有八瓦,萤火虫一般昏暗的灯光下,母亲给我们一家几口做棉鞋。首先是纳鞋底,鞋底用袼褙剪成鞋样大小。所谓的袼褙就是用旧衣服抹上玉米面熬的浆糊贴到墙上,待晒干后就取下来,这样处理后袼褙比较硬挺同时透气性还好。这样弄上三四层贴在一起,用白色的棉布延边,纳时先转两圈然后再纳中间。母亲纳起鞋底时看着毫不费力,母亲纳几针后把针在头发上划一下,静夜里只余母亲抽纳底绳时嘶嘶的声音。鞋底纳好后,絮上一层棉花,用棉布缝上即可。棉鞋的鞋扇是最难做的,母亲总是用条纹布做鞋面,里面再絮上洁白松软的棉花,上鞋面比纳鞋底更加费劲,但母亲总是做的很快,两个晚上一双崭新的棉鞋就上好了。用鞋楦楦好后就可以穿了。母亲做的棉鞋总是又暖和又漂亮,穿到哪里都能引来别人艳羡的目光,为此我常常暗自得意。可惜的是我的脚是水脚,跑得多了脚就会出汗,小时贪玩,一天下来,鞋底早已是湿漉漉的,晚上脱下鞋子,母亲就会在炉子上给我烤干,待我第二天穿时又是干爽暖和的。
1993年,我在外地上学,母亲送我时给我做了漂亮的塑料底棉鞋,可是那时候大多数同学都穿上了皮鞋,我穿着棉鞋总能招来别人异样的目光。那年秋天,母亲给别人家下苹果挣了40块钱,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,以35元钱给我买了双人造皮革的棉鞋。这鞋穿在脚上倒是暖和,但是不透气,穿了一段时间就捂出脚气。至于套袖,是再也不肯戴了,换成了毛绒绒可爱又暖和的卡通手套。我有了孩子后,母亲还给外孙做一些虎头鞋之类的,说是穿上养脚,给孩子做的棉衣总是自带套袖,棉衣袖口往前伸些弧度。
这几年,母亲眼睛花了,鞋是做不成了,偶尔给自己做双套袖,我回到家有时也戴,既温暖又自在。我对现在的生活挺知足的,告别了冬天与小伙伴撞衫的粗布棉袄,告别了棉鞋雪地进水后刺骨的冰冷,告别了一瓮酸菜过一冬的拮据日子,当然也告别了那个真正的冬天。我割舍不了的是母亲温暖的爱,困难时一家人的相互扶持,故乡的月亮和山峦。冬天来了,心里头涌上的是深深的怀念,村里头袅袅升起的炊烟,因雪的覆盖而寂静寥廓的山村,美的让人心无杂念,暖橙色的灯光下,母亲正低头忙碌,或是做棉鞋,或是缝套袖,简单又幸福。(计量检验中心 张建芳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