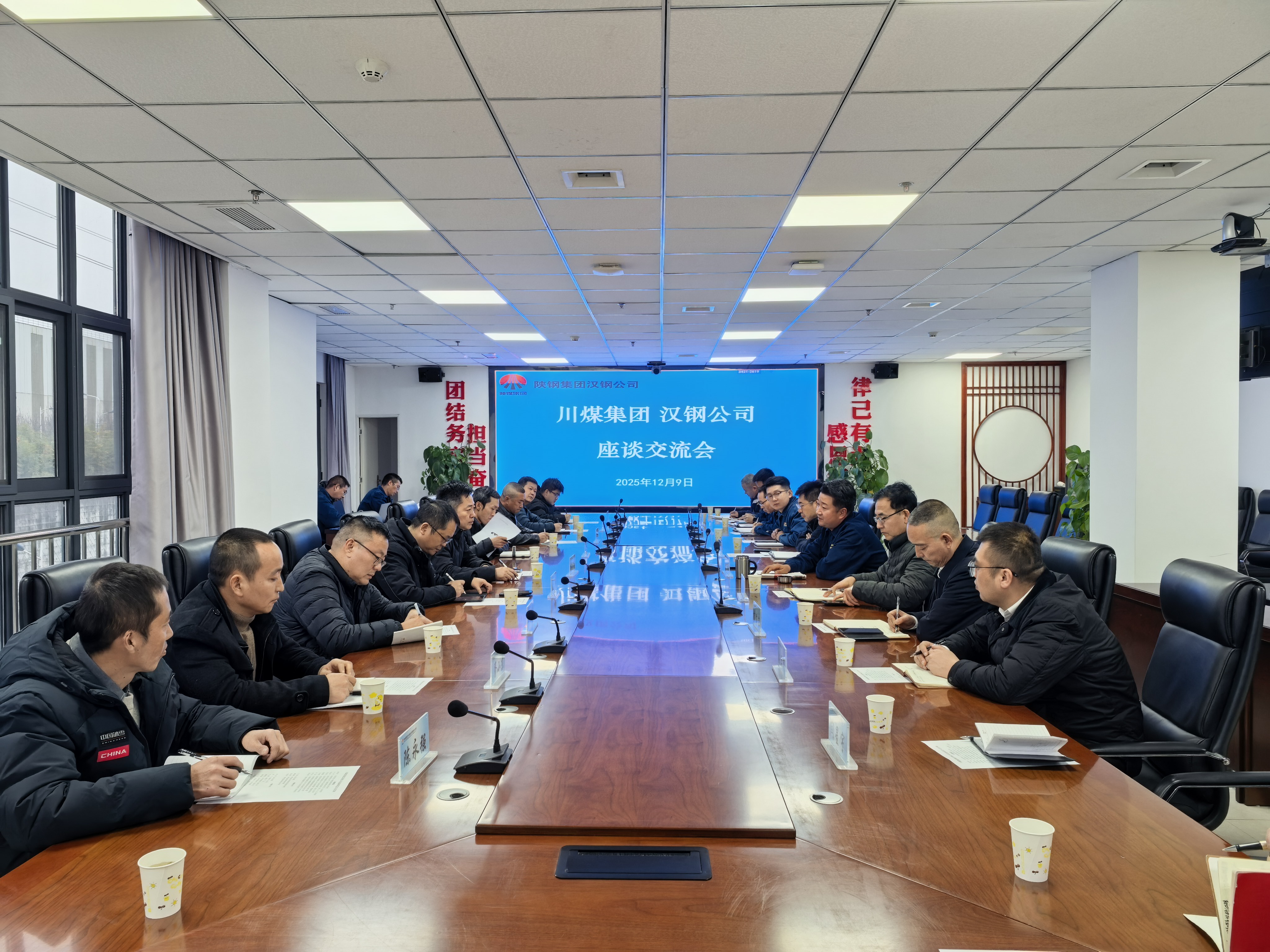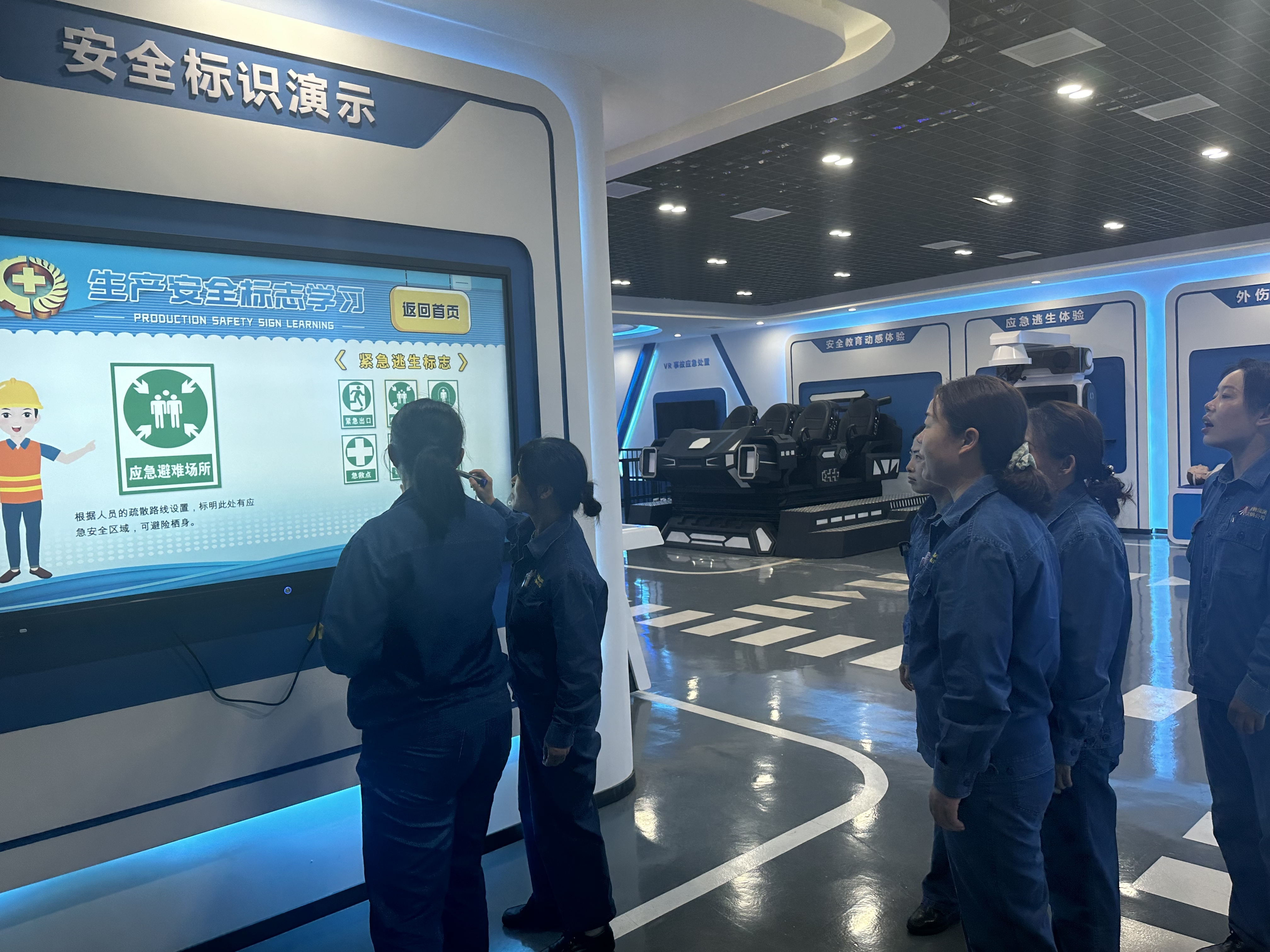北风附和着些许的阴冷,吹刮着轻柔的雨丝,冬雨的淅沥,混杂着春雨的味道,不过一种是安慰着荒芜,一种是催促着新生。都是略带寒意,身段柔美,不急不躁,就像一位经历沧桑看透世间沉浮的老者,语重心长地向我讲述着一种淡雅的高傲。
冬雨就这般下着,干渴的瓦片变得湿润,油亮,渐渐地雨水开始汇成了珠,串成帘,不知疲倦的在我的眼前,紧密地悬挂着,前仆后继地奔向羊肠小道,汇入门前的小河扬长而去,消失的无影无踪。冬雨的每一声嘀嗒,都有时间的间隔,好像是想让我们听一听它的回声是否美妙,也好像一位初学阶段的鼓手,一下击打,还要去询问声音是否响亮,力度是否可以,方式是否正确。这看似不自信的雨落,也布满了可琢磨的色彩。
每当冬雨来临,我便会撑起一把黑色的雨伞,顺着屋后的高坡走去。远望雨中的山丘、近处残余的绿色与我衰败的青春,这也是我一种习以为常的享受。远处山的一切都被雨水织起的薄雾笼罩着隐藏着,仅剩几条粗糙轮廓可描绘,但雨带来的朦胧美,又像极了我们对明天的迷茫,无知,探寻和追逐。近处的雨,抨击着田野里几颗被遗弃的白菜,它敞开着心房仿佛正在自嘲对我说:“我不是长不大的幼苗,我只是爱着冬雨的味道。瞧,这冰冷的雨它是多么的甘甜。”
时光推移,雨缓缓飘入了夜的幽暗,街巷开始寂静,高高的路灯为它的归宿指引着方向。窗外的嘀嗒声,被一些堆积的铁器无限放大,冬雨就这般的在我的梦中吵闹了一夜。(炼铁厂 王军